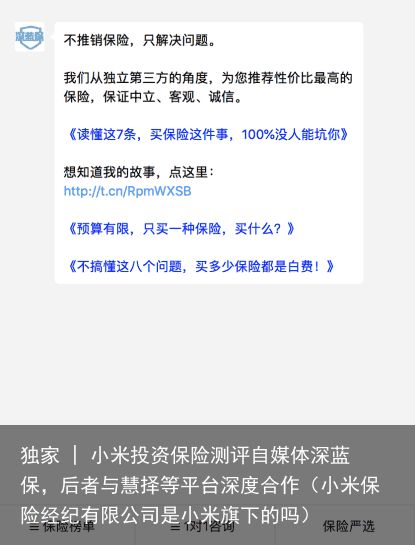第一次坐车(猫猫坐车呼吸急促)
李守柱
保宜公路横贯、蜿蜒在我家门前。打记事时起,公路上就行驶着南来北往的汽车,那时不比现在,车很少,很稀罕,偶尔看见一辆“北京”吉普,或者“伏尔加”轿车,那可了不得,都要驻足、翘首、远望,一直到消失在保宜公路的尽头。班车更少,最先的班车是解放牌卡车,上面绷有篷布棚子,车厢后面挂有梯子,旅客需要帮助,攀爬梯子上下。四方台学校附近有站,叫盘龙,因上下的旅客多,人们习惯把这里当站,而几公里之外的盘龙则鲜有问津,我们上学时都能好奇的围观。记得有一次宜昌葛洲坝的一辆大卡车,开到学校操场,教室里响起一片“啧啧”之声,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的投向这庞然大物,我们隔着窗子,引颈张望,羡慕不已。老师干脆下了课,一时间里三层外三层将大卡车团团围住,指指点点,议论纷纷。有个叫李爱明的杨家湾同学,他父亲是卡车司机,见多识广,他说这叫“十轮卡”,我们大家一数,果然是十个大车轮。卡车开走了,我们还追着在保宜公路上跑了很远很远。后来换成大客,前面是齐头的,白顶红身,远远的都能看见。车多了,班次也多了,近的到马良,到店垭,远的到宜昌,到神农架……据后来我们一位叫刘传明的同学说,他曾在红岩寺工作过,最无聊的时候就数班车,从保北发往保南的班车有十八班次,由保南开往保北的是十九班次,早晨五点到下午四点,川流不息。
“为什么会多一个班次?”
“有一班保康开往马桥的,去时从东流水走,返程则绕道歇马。”
从小学四年级开始,一直到初中毕业,在四方台学校读了五年书,但我没有坐过汽车。
初中毕业后,要到歇马街读高中,离家有二十五里地,学校一个月放一次假,一次放四天,星期六上半天课,放半天假,我们周六中午离校,夜里三四点钟被叫醒,睡眼惺忪的背着一周的粮食,两三瓶菜,怀揣父母给的零用钱,上路了。我从小跟爷爷睡觉,一般都是爷爷叫醒我,爷爷年轻时经常上工程,也要带米带菜,家里有一个“漆桶子”,木质的,上过漆,黑乎乎的,能装几大碗菜。我带过一次,同学们都笑话,漆桶斑驳、古朴,像个出土文物,确实有些别扭,还是用大口的玻璃瓶装好些。爷爷常常送我过河,到保宜公路后,再走一程,才把米袋和菜包挂到我肩上。
“快点走吧,路上别玩,鸡叫两遍了,今早起得晚,怕是要迟到了。”爷爷点燃旱烟袋,招着手,目送我走过龙潭沟。
过了龙潭沟就是土地岭,过了石板河就是沙岭寨。那里要离开公路,绕着大渠走一段小路,比从公路走要近好几里。然后,过铺子河,过良种场,过扁担湾,过烟袋岭,就进了歇马街。扁担湾路边有一口水井,冬天水是温的,夏天则是冰凉冰凉的,我们常常趴在井沿,一口气喝个痛快。二中是保康南边不错的学校,马桥、马良、两裕和店垭的学生,都在这里上学,学校每月放一次假,也是为了照顾这些远处的学生。我家并不宽裕,下面还有三个弟弟,两个还在读书,一个已经辍学,走路是很废鞋的,我们农村的孩子,一年四季都是穿“解放”牌球鞋,回家和上学都是穿旧鞋,上面有奶奶打的补丁,到了学校上课才换上新的球鞋。那时的球鞋质量很好,一双鞋穿一个学期甚至一年是常有的事,整个高一年级和这之前,我都没有穿过皮鞋,都是球鞋、凉鞋和母亲做的布鞋,直到高二时,同村同班的黄佳印同学,约我到横岭砍了一天柴,卖了十几元,才买了一双皮鞋。抚摸崭新的皮鞋,兴奋得睡不着,半夜起来摸一摸,比一比,试一试,谁知乐极生悲,皮鞋很硬,左右两边脚后跟和脚趾,都磨破了皮,血流不止。爷爷说,咱家穷,穷人穷命,穿不得皮鞋。那双皮鞋就随手扔在老屋的阁楼上,好多年以后,弟弟在老屋翻盖房子,我回家帮忙,还看见那双皮鞋,拿起、放下、又拿起。鞋子满是灰尘,两头翘起,变形的不成样子,当初买鞋的兴奋还记忆犹新,如今却是敝帚自珍,不忍割舍,“它的确没有什么价值了”,终于还是扔了。
歇马到盘龙的车票是两角钱,学校食堂的菜金是五分钱,我们自己带菜,很少也舍不得花五分钱买一勺菜,自然也舍不得花两角钱坐车。我到车站看过多次,但都没有坐过车。
(未完待续)
四月一日